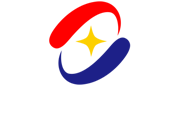2025年,苏良秀,95岁;达朋芳,87岁。
据公开报道,她们很可能是成都大轰炸仅存的仍在世受害者。她们在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,等待一份迟来的道歉。
从1938年11月8日到1944年12月18日,整整6年零40天。日本对重庆、成都、乐山、自贡、松潘等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,造成大量平民死伤,无数房屋被毁。
2006年,各地受害者以“重庆大轰炸”的名义,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,要求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,并进行道歉赔偿。2015年2月25日,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。2017年12月14日,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维持原判。2019年12月,日本最高法院终审仍维持原判。
从诉讼的角度来看,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已过去近20年。如果从1992年,重庆市民呼吁对日索赔开始算起,时间已过去33年。而从炸弹落下,万千家庭家破人亡的那一刻至今,许多人已带着战争伤痕,悲怆地走完了一生。

2025年8月13日,达朋芳接受四川在线记者采访。 蒋京洲 摄
巴蜀泣血
1941年7月27日,成都的天黑了。
上午11时45分,日本海军航空队108架轰炸机遮天蔽日,分四批向成都市区投下炸弹。城市陷入火海,建筑化为废墟。死难者的鲜血染红锦江,重伤者的呻吟惨不忍闻。
苏良秀右腿触目惊心的伤痕,是日寇战争罪行的铁证。
“我家的7人和3个亲戚,都在我家房后的一棵核桃树下躲避。一颗炸弹从天而降,我的祖母、母亲、孃孃、表孃、大弟、二弟被当场炸死,我也被炸弹炸伤……我腿上的伤口里都长出了十多条蛆,医生用镊子帮我一条一条夹掉,告诉我不要再让苍蝇接近伤口,我就只能用被子一直盖住受伤的腿,不管天气再热都不敢掀开。”
苏良秀的表妹达朋芳,在“七二七”成都大轰炸发生时年仅三岁。她在逃命时被大人拉扯,手臂脱臼,因未得到及时救治而落下终身残疾。“好好的一个家,就这样支离破碎。你看我这左手,根本抬不起来,这一辈子都这样了。” 达朋芳说。
十三岁的张明锦,从硝烟中爬起,看到的景象如同地狱:“我看见妈妈左眼被炸伤,血从眼眶里不断外流,只有抱在妈妈怀中的妹妹没有受伤。但是我父亲头被炸伤,样子很难看地死去了。我的姐姐也死了。”
那一天,炸弹撕碎了上千个家庭,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。家破人亡,生离死别。翻开四川省档案馆编《川魂——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》,这样的景象,在1941年的四川几乎每天都在上演:
7月27日,成都。敌机108架,投弹426枚,烧夷弹20枚,伤905人,亡689人。
7月27日,绵阳、遂宁、阆中、三台、梓潼、万县、简阳、南充……
7月28日,万县、自贡、泸县、内江、忠县……

徐斌、苏良秀、马兰(苏良秀女儿)、老田(化名,日本志愿者)等人在日本东京合影 徐斌供图
箭在弦上
1990年,北京学者童增发表论文——《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》。
山雨欲来。1992年,重庆市民请求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民间对日索赔问题。同年,重庆大轰炸的两名受害者自发采取对日索赔的相关行动。
这一年,学者刘世龙就职的重庆出版社出版了《重庆大轰炸1938-1943》。两年后,刘世龙旅日留学,其间,他读到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教授横山英译为日文的吴嘉陵著《日本帝国主义空军轰炸四川的罪行》一文。
在广岛的另一件事,进一步坚定了刘世龙为大轰炸存史留证的决心。“我去广岛和平纪念馆,看过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名册,其梳理之清晰、记载之详实令人感叹。如果重庆大轰炸这一历史惨案的情况长期不清不楚,既不能明辨是非,也无法告慰亡者。如果有人否认,我们能否拿出证据来驳斥?”

成都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成员在日本东京街头进行宣传。 徐斌供图
与此同时,日本方面一批有良知的律师也在行动。
土屋公献,1943年作为学生兵加入日本海军,亲眼目睹许多同学战死。战后,土屋公献进入东京大学法学部学习,后成为一名律师。自1995年开始,他担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日本辩护律师团团长,后又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辩护。
2002年12月13日,另一名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接受委托,成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的代理律师,开始对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进行访谈取证。
2004年12月,一濑等多名日本律师到访重庆,开始首次对大轰炸受害者进行访谈取证。同年12月,一行人访问成都,调查成都地区的受害事实。这些浸透血泪的控诉,成为日后庭审中的关键证据。
2005年,土屋公献罹患癌症。直到2009年去世前,他仍在关心731部队细菌战和大轰炸受害者索赔诉讼案件的进展。他把一切托付给一濑敬一郎,请求他斗争到底。
多年的涓滴努力,在此刻汇聚成河。一场注定艰难的跨国诉讼已箭在弦上。

2005年12月30日,刘世龙教授、一濑敬一郎律师、权田茂(湖南文理学院日籍教师)在成都市春熙路合影。此行他们商议成都、乐山、自贡、松潘等地大轰炸受害者寻访和档案报刊调研等重要事项。 刘世龙供图
东京审判
2006年3月30日,诉讼团代理律师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,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作为原告,起诉日本政府,要求其对各原告谢罪,并支付一千万日元赔偿金。
法院立案。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开始了!
受害者们不断涌现。2008年7月、12月和2009年10月,诉讼三次追加,原告从最开始的40名已增至188名。

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裁判现场。 徐斌供图
受重庆大轰炸成都地区诉讼团团长文仲委托,四川君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斌成为成都地区诉讼团的代理律师。“因为我是南京人。”徐斌告诉记者,“我的爷爷、奶奶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。路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,奶奶说什么也不肯进去。她的一个好友在南京大屠杀中失踪了。她一直在害怕,怕在遇难者名单上,看到那个熟悉的名字。”
2006年10月,东京地方法院开始第一次庭审。法院要求,各原告须从中国到日本出庭。
当时,许多原告已年近耄耋。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赶赴东京出庭的决心。他们自筹路费,甚至孤身一人,前往异国讨要一个公道。

2014年6月,东京大轰炸牺牲者遗族召集座谈会,欢迎苏良秀老人赴日。 徐斌供图
2012年9月,74岁的达朋芳决定开始“一个人的远征”——孤身前往日本出庭作证。
“一个成都老太婆要去找日本人算账!”她的故事流传开来。同年10月,她站在了东京的法庭之上,40分钟的陈述,字字浸血。
一濑敬一郎告诉记者,日本民众对此次审判非常关注。在东京地方法院的31次庭审中,每次近100个旁听席都座无虚席。因人数太多,旁听的日本民众只能抽签进入法院。还有更多的人守在法院外声援。
妨碍诉讼的声音同样存在。徐斌说,一次出庭结束回旅店路上,一伙穿着旧日本军队制服的人,开车绕着他们打转,并用高音喇叭辱骂。还有一次,有人将点燃的鞭炮扔在一濑敬一郎律师身上,大骂他是“混蛋”。
法庭内的斗争同样激烈。一濑敬一郎回忆,2013年,法院单方面认为人证没有必要再出庭,“这是粗暴地完全否定原告的审判斗争,绝对不能承认。”为此,原告团、辩护律师团用明信片和传真要求法院采用人证,并在日本和中国各地开展签名征集活动。
“从中国过去的传真把东京法院的传真机都弄坏了。”徐斌说。同年11月,法院同意选取5名中国学者、4名日本学者、6名原告共计15人作为人证。

苏良秀和前田哲男(日本记者,专家证人)、刘世龙于2014年6月4日到东京地方法院出庭举证成都大轰炸受害实情的海报。 刘世龙供图
从2006年提诉讼,直至2015年。漫长的9年间,东京地方法院前后总共开庭31次,188位原告的血泪控诉,终于全部呈现在法庭之上。
2015年2月25日,下午三时,东京地方法院第203号法庭,一审宣判。在200多页的判决书里,详细记载了法庭调查确认的加害事实。然而面对如山铁证,法院却以《中日联合声明》等文件中,中方对于战争赔偿请求权的放弃为由,驳回原告方的诉请。
2017年12月14日,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维持原判。2019年12月,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宣判维持原判。由于日本是三审终审制,这意味着至此本案诉讼在日本已“尘埃落定”。